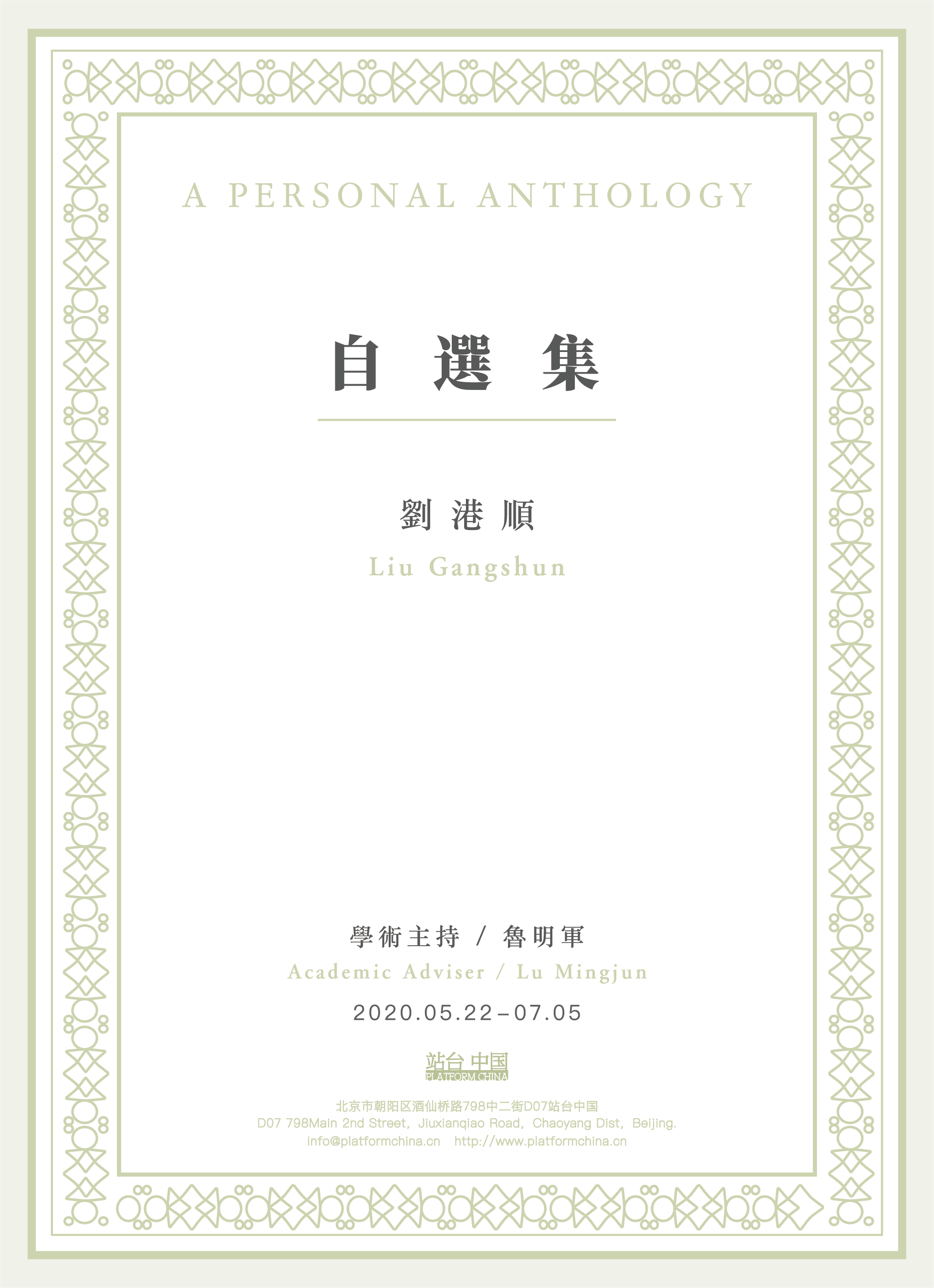
文本作为绘画母题并不鲜见,古往今来,这样一种撷取和转换方式原本就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惯例。不过对于大多艺术家而言,它往往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或只是作为绘画的一个手段,而在刘港顺这里,收集文本,从中选择图像和母题本身便构成了他绘画语言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他的日常生活本身。
刘港顺的目光所及和所描绘的对象多非现实,主要来自某个图像文本或某一时刻的阅读体验。也正因如此,他的这一系列绘画自始至终就带有“画中画”的特征,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所有的绘画都可以归为“元绘画”实践。当然,刘港顺的绘画并非是教条、僵化的“画中画”图式,他在绘制中尝试了多种可见或不可见的自我指涉机制。
“蜜蜂的寓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大多文艺青年一样,刘港顺也曾迷恋欧美前卫艺术和先锋文学。1995年,他在湖北黄石开了一家名为“后人类”的独立书店,也是在这期间,他经受了种种激进思想和实验文本的洗礼。曾经一度,他狂热过,也愤怒过,他反抗过,也绝望过,他幻想过共产主义,也期待过自由主义的大同,甚至还着迷过一段时间的无政府主义……直到2002年,年近不惑的他关掉书店,只身来到北京,全心投入绘画的时候,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激情四射的青春年代,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断:将过去的经验和情绪彻底从自我的身心内部抽离出来,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可分析和可理解的对象或物。
2004年的《从约翰斯开始的一年》重启了刘港顺的绘画道路,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他临摹了一组贾斯珀·约翰斯于1985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四季》的文本。约翰斯后来多次出现在他的画面中,对于刘港顺而言,约翰斯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在约翰斯作品中看到了人生的隐喻,《从约翰斯开始的一年》也成了他北漂的起点。这其中,更重要的还体现在约翰斯画面中的“物化”和“去人性化”这一特征。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曾敏锐地指出:约翰斯的高明就在于他终结了错觉绘画,在他的画面中,油彩的处理不再被当作一种转化(transformation)的媒介;它不只是对人类主题的一种无视,就像抽象艺术一样,还有一种缺席的暗示,一种人造环境里的人性的缺失。于是,只有物品——人造物的迹象被遗留下来,在人类的缺席中,这些迹象最终成了物品。这一方面表明一种新的艺术创造曲折的受众过程,另一方面它提醒我们,这种冷漠与荒芜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正是这一点,暗合了刘港顺当时的心境和选择。这固然是一种绘画本身的实验,但对他而言,毋宁说是一次自我生命的检省。自此,曾令他身心澎湃的激浪派、鲍勃·迪伦,开始变作他理性分析和描绘的文本母题。
诚如艺术史家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所说的,每个艺术家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它可能是某个真实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也可能是艺术家的画室,抑或是书架,还有可能在艺术家的头脑里。刘港顺也不例外,他的博物馆在画室,在书架上,在头脑里。曾经伴随他的画册、小说、诗歌和理论著作成了他收集绘画素材的主要途径。作为手段的“收集”,既是他绘画的程序之一,也是他绘画语言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在他的画室,或展览的现场,马列维奇、基彭伯格、沃霍尔、贾斯珀·约翰斯、博伊斯、阿尔伯斯、河源温、迈克尔·海泽、理查德·塞拉、辛迪·舍曼、培根、利希滕斯坦、克莱因、波尔克等艺术家的经典之作汇聚一室,纵横交织,无序地“崩现”,仿若一部运动中的20世纪艺术史。
作为“元绘画”的最初形态,“收集”既是一种绘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知识机制。且早在17世纪,这样一种“画中画”形式便盛行于佛兰德斯,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鲁本斯与扬·勃鲁盖尔合作的系列“藏珍阁”(Cabinet of Curiosity)绘画和特尼尔斯(David the Younger Teniers)创作的一系列“画廊画”。如鲁本斯和扬·勃鲁盖尔合作的《视觉的寓言》(1617),这是一幅典型的“画中画”或“元绘画”。艺术史家斯托伊奇塔(Victor I. Stoichita)敏锐地发现,不仅只此,画面中的母题之一“花”本身便带有“收集”或“集合”的意思。“花束”即“收藏”,上面的蜜蜂暗喻着一种“炼金术”,而画家在此扮演的则是“花农”的角色。这样一种形式及其隐喻回应了17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全知”运动,同时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实践,也呼应了同时期思想家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蜜蜂的寓言》中关于花与蜜蜂及其生产性的论述。蜜蜂在花朵之间飞来飞去,采集花蜜然后运回蜂房,在蜜蜂采集花蜜的时候,它的腿会摩擦并沾上花粉,当它飞到另一朵花上的时候,腿上的花粉会沾染在下一朵花上。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奇异性的相遇和主体性的生产,形成了一种新的组合,并构成了诸种共同性的新形式。
就像蜜蜂一样,刘港顺也是一个图像(知识)的采集者、生产者和“冶金者”。当然,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普遍的知识生产和图像传播的方式。而在刘港顺的心目中,不仅只有一座博物馆或美术馆,还有一座图书馆。除了以上所述的那些艺术家的经典之作,罗伯-格里耶、卡明斯、居伊·德波、贝克特、雷蒙德·卡佛、托马斯·曼、雷蒙·格诺、萨特、亨利·米勒等作家的文本中的只言片语也是他作品中的母题之一。这样一种方式让我想起一百年前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和犹太思想家本雅明的实践。上世纪20年代,瓦尔堡建了一座意图打破既有学科分类体系的图书馆,并开始着手实施与之相应的《记忆女神图集》计划。这个未完成的计划可解释为同时期思想家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拼贴的视觉对应物。和瓦尔堡一样,本雅明也喜欢买书、藏书,也期待拥有一座图书馆。据说,他原本还想写一部完全由引文构成的著作,遗憾的是,这一愿望在他生前并未实现。刘港顺虽非受到瓦尔堡和本雅明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但他的方式(包括开书店)倒像是前者的延续。不同的是,刘的“引文(图)组装”及其“断章取义”并非诉诸某种叙事,也不是针对某个既有的系统,他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只言片语所传递和释放的不确切的感知与观念。而这一点便首先体现在复杂多变的词图关系中。
词与图
和“元绘画”一样,词与图的关系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经典命题,甚或说是“元绘画”的一部分。本文无须追溯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刘港顺的实践也与之并无直接的关系,相形之下,他的词图组合似乎更加“简单粗暴”,却又恰如其分。
词图互文是刘港顺画面中最常见的一种语言。在《基彭伯格的肖像》(2008)中,他用最朴素的写实手法,描绘了基彭伯格的经典画作《侍者…》(1991)。这盏落地灯曾多次出现在基彭伯格的绘画和装置中,正是在这盏弯曲的落地灯中,刘港顺看到了基氏命运多舛的一生。不过,刘港顺描绘的并非是展览的现场,而是来自一本画册,他在画面上用黑体标注了“Kippenberger”,这一词图关系一方面暗示弯曲的落地灯就是他眼中的基彭伯格,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这只是一个文本,甚或是一本基彭伯格画册的封面。《这不是万宝路》(2006)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画面的主体是荷兰风格派画家杜斯伯格(Theo van Doesburg)的名作《综合XI》(1918),不过,刘港顺援引这一母题的时候,将其全部换成了黑色。表面看,它更像是马列维奇的“黑方块”,画面的下边,并排描绘了两个万宝路烟盒的局部,并用“Malevich”代替了“Marlboro”。
1922年,杜斯伯格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方块就和早期基督教徒的十字一样。”同年,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方块终将征服十字。”另外,许多风格派成员也都在写作中频繁地提到“精神性”。作为“至上主义”的标志,“黑方块”被马列维奇视为一种超自然的形式,从而赋予它某种神秘和宗教色彩。“万宝路”所指的自然是美国消费意识形态,这意味着,“Malevich”在今天已经像“Marlboro”一样成了一个被消费的符号,反之,作为消费意识形态的一个象征,“Marlboro”业已和宗教无二。可见,一方面神秘的“黑方块”成了表面的消费符号,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波普作为宗教的一面,所谓“拜物教”也是一种宗教。若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容忽视的是,风格派原本与形式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表面看形式主义将形式与物对立了起来,但实际上,形式主义的前提是将作品“物化”和“去人性化”。而在这一点上,其实与波普并无本质的不同。不过,刘港顺真正着迷的显然不是其物的一面,而是内涵在客观之形式和物背后的精神性和意志力。马列维奇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画面中,在《俄罗斯》(2007)中,画面背景就是一个“黑方块”,画面中间用黑体白色书写着“RUSSIA!”,对于艺术家而言,“黑方块”就是俄罗斯的精神,但有意味的是,他并没有用中文,也没有用俄文,而是用英文书写“RUSSIA!”。因此,文字与背景图像之间看似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又同时暗示着二者之间的某种分裂。
词图关系并非仅止于象征层面,有时候色彩和形式感知也是图像的一部分。比如“诗人”与灰色背景,“简单”与蓝色背景,“木头木炭”与黄色背景,“艺术无用回家吧”与红色背景,“生活真危险”与白色背景……这些色彩与文字之间看似没有关联,但实际上我们对于背景色彩的感知直指文字内容。“绝不工作”是居伊·德波的一句名言,在1952年到1972年之间,他发起的前卫运动(字母主义国际和境遇主义国际)猛烈地冲击了整个西方世界。他确实没工作过,甚至不屑进入大学接受科班教育。他喝酒、逛街、写作、拍摄电影,甚至用怠工和停工来抵抗堕落的社会。1967年,他的《景观社会》一书为翌年爆发的“五月风暴”播下了思想的火种,“绝不工作”这句宣言便出自这本小册子。刘港顺的《绝不工作!》(2012)并没有刻意做图像处理,这里的文字本身就是图像,不过他所采用的画幅形制包括字体像是传统劳动和事业单位的门牌,因此,一方面形式上二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又隐含着一个极端的分裂和冲突。在新作《“当心!”》(2019)中,蓝色背景的画面中心写着两个浅灰色黑体字“当心!”,他刻意保留了为了控制字形和大小而提前绘制的格子,特别是长短不一的线条及其笔锋,隐隐暗示着某种危险和不确定。此时,词与图是一致的,或者说词本身即是图或是其中的一部分。
并不是所有的画面都有文字或概念,也有一部分作品只有图像。据艺术家所言,这些图像实际上都源自某个文本。《世界》(2019)源自美国艺术家迈克尔·海泽的大地艺术作品《复合一/城市》(图片)的一个局部,刘港顺强化了画面的构成感,特别是其硬边处理手法和有秩序的区隔及其疏离感,一方面与远山构成了一种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也隐隐透着某种暴力和危险。海泽曾说:“急迫、苦难、戏剧性、冒险性是做艺术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的作品,“如果是好的,肯定有关‘危险’,如果不是,它便寡淡无味”。刘港顺的描绘与其说是对于这张作品图片的重新演绎,不如说是对于海泽这段文字的视觉阐释。在海泽的作品图片中,我们不难洞悉作品所在的美国内华达州荒漠的地貌,以及作品所释放的力量,而在刘港顺这里,他抽掉了这一背景,荒漠地貌被概念化成几何构成,白色线条隐喻着速度,并凸显了前景中并排的三角形体装置及其影子所传递的力量和危险,及其普遍的一面。与之相应的是另一件作品《世界工厂》(2015)。它源于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非虚构作品《打工女孩》,她曾花了数年时间,跟踪采访工作生活在东莞加工厂的打工女孩们的生存现状和命运。作为“世界工厂”的标志,东莞曾缔造了一个神话,一度被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隐喻。然而在刘港顺的笔下,它被描绘成一座废弃的厂房,仿佛一座荒芜人烟的孤岛。刘港顺创作这幅画作的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已经成为历史,而此时,那些曾经在此挥洒汗水和青春的工厂女孩去了何处?现在又在哪里?或许,这才是刘港顺真正想表达的。
如果说在《世界工厂》中,刘港顺描绘了一座废弃孤岛的外景,那么在同年完成的《1984》(2015)中,他所刻画的仿佛是这座孤岛内景的一部分。画面描绘的像是盥洗室的一角,右边是一个小便池,左边是无水的洗手池,这样一种幽闭让他想起了奥威尔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中抑郁、窒息的气氛,而画面斜俯视的视角暗示着它可能源自“老大哥”的目光。事实上,“1984”是把1948年的“48”倒过来读,展望三四十年后的情景。今天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奥威尔在书中所幻想、预言的无所不在的强权和监控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和习惯。而当疫情降临时,全民的隔离成了现实,意识形态的区分也已然失效。画面中的小便池和洗手池仿佛悬在空中,这也赋予画面某种超现实感和想象的空间。对于刘港顺而言,绘画与其说是用来凝视和感知的,不如说是用来思考和想象的。在这里,它隐含着一层不可见的词图结构,而无论是词图之间的分裂,还是词作为图或图作为词,无不反身指向绘画本身,这也是其作为“元绘画”实践的一种体现。
反绘画—体制
2000年初,当刘港顺重新拿起画笔的时候,便决定彻底清除掉残留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遗留下的狂热情绪,于是,他不仅将绘画视为一个理性分析的对象,同时,在具体描绘的时候,也尽量将情绪压到最低限度,以彻底剔除体现在画面形式或媒介中的情绪。这样的方式并不鲜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培力、耿建翌的系列观念绘画就已经带有平涂风格和反绘画的色彩,同样,刘港顺的平涂也是一种反绘画或观念化(概念化)的体现。
显然,从选择文本作为素材到画面中的文字,皆表明刘港顺的绘画实践更接近概念艺术,况且,索尔·洛维特、河源温这些概念艺术家的作品原本也是他曾挪用的对象。说到“概念艺术”,事实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新前卫艺术浪潮及其去物质化的特征原本是反商业、反战运动的一部分,即便是使用绘画的媒介,对他们而言,绘画本身也非目的,然而在刘港顺这里,尽管概念是他语言的一部分,但他的目的不是去物质化,最终还是落脚在绘画,甚或说,他自认为还是一个画家。可即便如此,在他的绘画中还是含有各种反绘画的意图和特征。在这里,反绘画不仅是绘画的一部分,并反身指向绘画本身。换句话说,反绘画的绘画也是一种“元绘画”。
早在1993年,在《油画颜料》这幅画中,已经暗示了这一自我指涉结构。画面用写实的手法描绘的是颜料盒的局部,也许是因为来自某个文本,他将色彩处理成黑白灰。显然,这里的“颜料”不仅是描绘的对象,同时也反身指向了绘画本身。同样,早在17世纪的时候,佛兰德斯画家基斯布瑞奇(Cornelius N. Gijsbrechts)便已将绘画工具或媒介作为对象或素材绘入画中,在斯托伊奇塔看来,这也是绘画诉诸自身或主体化的一种方式或路径。如果说其画中反复出现的调色板是一种悖论性的自我指涉的话,那么在另一件作品《转向背面的绘画》(1670-1675)的时候,这一悖论结构则彻底消失了,从而转化为一个“无中生有”的视觉机制。基斯布瑞奇并没有将一幅画反转后展示给公众,而是直接画了一幅画真实的背面。于是,这幅画的背面变成了一幅画,绘画本身便成了画家描绘的对象。而作为一种“元绘画”实践,这一否定性的反转或颠倒则以彻底去主体化的方式重塑了主体。三百年后,美国波普艺术家利希滕斯坦也画过一幅绘画的背面。不过在利希滕斯坦这里,绘画的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从而也更加明确地指向绘画本身。
刘港顺尽管没有基斯布瑞奇和利希滕斯坦如此绝决,但在2009年创作的“尺寸”系列作品中,并不乏相似的语言逻辑。在不同的底色的画面中,他用不同颜色的黑体书写了画幅的尺寸,比如“68×120cm”“80×110cm”“90×150cm”等,它既是画幅尺寸,也是作品的标题。这虽然只是一个语词或概念,但它同时也是画面内容,并反身指向绘画本身。对于这一反绘画的绘画,刘港顺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尺幅对于绘画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艺术资本的时代,尺幅是衡量艺术价格的重要参数之一。刘港顺说,这是“自主的艺术现实”,它取决于画面题材、内容或风格,而并非画外,比如市场、资本等。或许,他这一系列作品所表述或质询的正是这一点。也正因如此,它的确比较接近作为“新前卫”的概念艺术或体制性艺术的实践。
20世纪以来,美术馆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系统构成要素之一。作为一种权力机构,它们仿佛是艺术帝国的顶层,不仅缔造了艺术史,同时也是艺术资本的隐形合谋者。而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无论MoMA、PS1,还是古根海姆,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心向往之的“圣殿”,都曾梦想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进入这些机构或举办展览。刘港顺一直对此心存怀疑,不过,他并没有去刻画我们是如何向往这些“圣殿”的,如在《P.S.1》(2007)和《古根海姆美术馆》(2014),通过描绘它们的Logo和建筑,从而将其文本化、符号化或概念化。在《MoMA》(2016)中,刘港顺将2005年艺术家艾默格林(Michael Elmgreen)与德拉塞特(Ingar Dragset)在德克萨斯荒漠中某小镇上创作的“普拉达商店”的Logo“Prada Marfa”换成了“MoMA”,对于这一达达式的巧妙置换,我们固然可以说,此时艺术既是自然,也是商品。但刘港顺这里所描绘的更像是我们与MoMA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而他真正想传递的不是对于它的向往,恰恰是对于这种心态本身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荒漠中的这座“MoMA”仿若中国当代艺术系统的隐喻,它既没有群众基础,但在外人的眼中又高度商业化,而这本身就是一个诡论。当然,刘港顺眼中的“MoMA”终究只是一个文本,一个他收集和撷取图像母题的普通容器。而对于画面的自我指涉机制而言,它不仅体现在文本性,也体现在它的(反)体制意识。
说到“(反)体制”,在刘港顺这里,它并非单指整个艺术系统,绘画(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顽固的体制。而他的实践主要针对的也是后者。新作《云彩》(2019)是一幅去绘画的绘画,画面的母题源自《云彩收集者手册》一书的封面,刘港顺在绘制中,取掉了近景中的杉树,凸显了云彩和橘黄的天空,并有意将画面处理成印版的视觉效果,如果不加细看,观者会误以为是印刷品。和“尺寸”系列一样,画面提醒我们,看似不是绘画,但它就是绘画。印版效果指向了图像的文本来源,同时也反身指向绘画本身。绘画即文本,文本即绘画。“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刘港顺的绘画无疑是德里达这句名言最恰切的视觉注脚。
余说:“作者之死”?
2010年,在《灰烬》中,刘港顺描绘了一副蓝天白云的景象,并在上面写了两个红色的黑体大字:灰烬。刘港顺说:“在蓝天白云下,飞灰烟灭是绅士的理想。”这里的“绅士”或许是一种自我暗示,并由此将自己彻底从中抽身出来,或随着画面一同化为灰烬和虚空。也许,它所暗示的正是巴特所谓的“作者之死”。在巴特看来,文本是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等等的产物,而作者,仅仅是将文本从这些背景中汲取出来。只有文本被创作出的时候作者才成为作者,作者的存在既不先于文本,也不后于文本。也因此,文本本身,除了是由语言编织而成的产物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由作者附加的)意义。刘港顺刻意地将自己的作品简化到最低限度,并通过多种语言形式用来抵制被归于某种风格或派别——尽管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相对明显的特征和取向。事实上,刘港顺是希望将自己与绘画分离开来,他关心的是还是文本与话语的构成。他虽然并不拒绝各种解释的介入,甚至有意地传递一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感,但这些都不是为了附加他个人或现实的某种意义,在他眼中,这原本就是文本的属性。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文本的“延异”,一种文本的“再生产”。按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和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话说,这是一种彻底瓦解了“原创性神话”的“后制品”(Postproduction)。
“一切归于尘土”,“一切归于寂静”……这是刘港顺两幅作品的名称,前者取自老子的《道德经》,后者是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谚语。前者的背景中间是一条图像带,约占画面三分之一,图像描绘的是一幅绿色为基调的街景,上下各三分之一的部位留空,仿佛中间图像部分是被上下挤压出来的,又像是上下的空白在逐渐吞噬着原本完整的图像,或许这才是“归于尘土”的真正寓意。后者的背景图像源于卡茨的一件作品,也有他对宋庄北塘湖畔的畅想。他说:“一切都归于寂静,这是一个恒常的道理。”而在此,无论是背景中的图像,还是前面的文字,皆传递着一种虚无感,就像他另一件作品所示的:“一切皆错。”
2007年的《空虚》描绘的是1960年克莱因经典的同名行为照片。这张照片发表后,成了行为艺术的发端之作,同时也是人类迈向虚无的天真尝试。克莱因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所想到的总是与空虚联系在一块,我肯定是在空虚的中心,如同在人的心脏,有火在燃烧。”刘港顺在此描绘的与其说是克莱因的行为照片,不如说是一种虚空。一切归于虚空,“未来即幽灵”。吊诡的是,虚空本身就是我们所身处的现实。如果由此将刘港顺定义为一个虚无主义者,还是过于消极了一点。就像他在表征虚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追溯体现在“至上主义”“风格派”以及包豪斯身上的精神性和意志力,对他(乃至所有人)而言,真正的困境不是由此创造一种应对和抵抗虚无的精神形式,而是如何将这样一种分裂体现得更为极致,更加彻底,进而从中找到一条行动的道路。





















